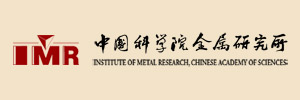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多少应该保留的记忆,都被流逝的时光冲洗得模糊、黯淡、忘却了。而我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前后这段经历却永远印刻在脑际,五十年后回忆起来,还是那样清晰,那样鲜明,历历在目,如同发生在昨天。
1951年,南京、芜湖两地大学毕业生的学习班持续一个月,到8月中旬结束了。学员来自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安徽大学等高等院校本届毕业生。南京大学的毕业生最多,学习班就设在该校。办班的目的是让学生树立以国家的需要为自己的志向,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的思想。据说上一年的毕业生就有的在高薪诱惑下,走进了私人企业,未能服从组织分配。学习班学习生活安排得轻松合理。听报告、学文件、座谈讨论,还时而开展文娱活动,游览名胜古迹。学习班一结束,就公布了各人的去向。我被通知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筹备处工作。地点在北京。
去北京工作的同学真不少,8月22日在南京车站上车时,坐满一节车厢。8月24日下午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北京刚刚下过第一场秋雨,清凉之气沁人心脾,从南京带来的溽暑和两天旅途的困顿一洗而空。
到达科学院集体宿舍稍事安顿后,我就赶往科学院办公厅报到。在会客室坐定不久,张沛霖先生就来了。张先生是半年前从英国回来的,在天津北洋大学担任教授,兼顾冶金所的筹备事宜。张先生当年30出头不多,身材修长而挺拔,穿件深色西服,没有系领带,简洁中透出潇洒,昂藏里不掩清灵,令人联想起“玉树临风”。
张先生说话较慢,吐字清晰,略带山西口音,音调中透露出北方人的爽直和真诚,让我感到亲切和温暖。他表示欢迎我到冶金所筹备处工作。在他的引领下我到了中科院冶金所筹备处,同时见到了筹备处主任李薰先生。李薰先生刚从国外回来。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一只转椅上,左手握着烟斗,不时地吸几口烟,和气地问起我个人情况。当他说到兴建冶金所时,转过身去,指着身后墙上的一张挂图说:“这就是冶金所的外观图,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实验大楼。”这时,我才看清楚,那是一张水彩画。画中央是座颇为雄伟壮观的四层大楼,门前停放几辆轿车,天空中飘浮着几抹白云,楼前花园里百花盛开,姹紫嫣红。望着这不久将来就要出现的现实,令人感到振奋。
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部在文津街3号,是座L形的三层红砖建筑。在L的短臂上有半地下室,地下室的尽头是财务处,与其毗邻的两间房子由冶金所筹备处占用着。51年8月间,除李薰先生和张沛霖先生外,张作梅、方柄先生也由英国回到北京,前来冶金所筹备处报到上班了。在我之前几天,已有四位应届大学毕业生到来了。他们是李铁藩、张子青、吴汶海和俞焕钦,一共有了9个人,筹备处也就初具雏型了。
不久,科学院召开第二次院务会议,每次大会都让我们年轻人去参加。郭沫若院长在报告中说,根据李薰博士的建议,决定将正在筹建中的冶金研究所改为金属研究所。从此,我们筹备处就称为金属研究所筹备处了。这个建议和决定是高瞻远瞩的,它为科学院内与冶金科学技术有关的几个研究机构的协作分工做出了合理安排,更为金属所的发展拓展出广阔的空间。
郭沫若院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文学家。他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不杂四川口音,且音调清亮、圆润,十分悦耳。我一面听着郭院长的报告,一面遐想着,假如由他朗诵他的传世之作《女神》,一定会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收到震憾心灵的效果。会上,还看到了陶孟和、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几位副院长。他们都是我久仰的著名学者。陈伯达也是副院长,我已读过他写的《四大家族》《刽子手曾国藩》等著作,但从未见他参加过大会。
李薰先生、张沛霖先生都是著名的冶金学家。李薰先生1937年去英国设菲尔德大学冶金系读学位,学成后就在该系工作。在那里生活了14年。新中国成立不久,郭沫若院长致函李薰先生,邀请他回国创建金属研究所,他欣然接受,并在英国邀集友人商讨,为金属所的创建做着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李薰先生是最早研究钢中氢问题的学者。张沛霖先生稍晚也加入了那个研究集体。氢,这个自然界重量最轻、结构最简单、体积最小的元素,却对钢具有极大的破坏力,由此引发出很多灾难性的机械事故。这个研究集体精深的研究成果阐释了氢的破坏规律,并且开了60~70年代兴起的氢对其它金属损伤研究的先河。李薰先生逝世后,化学家邹元火羲 先生曾写诗纪念李先生道:“海外扬名早,辽东创业精。”前句就是指他早年关于钢中氢的研究,后句是指他创建金属研究所。
筹备处的四位先生都是三十几岁,李薰先生年纪最长,当时也只有38岁,但在我们这几个刚走出校门的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眼中,他们都是长者。他们关心着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关心着我们的进步和成长。张沛霖先生了解到我们几个人都不是学冶金专业的,缺乏这方面的基本知识,就指定我们每人阅读一本专业书。隔一段时间还让我们复述书中主要内容,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又有计划、有针对性的邀请有关学者为我们讲课。当时没有讲课费一说,也没有小车接送,只有清茶一杯,但讲课的学者都非常认真,使我们获益不浅。给我们讲课次数最多的是葛庭燧先生。他从金属结构讲到金属形变。葛庭燧先生早已是著名的科学家。40年代,他就以金属内耗的卓越研究成果而蜚声国内外。新中国一成立,他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回到祖国,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授,为新中国培育人才。张沛霖先生还领我们到清华大学参观过葛先生的内耗实验室,拜访了葛先生的家,见到了葛先生夫人何怡贞先生。何先生时任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还见到了葛先生的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运培和运健。当年姐弟二人都在清华园托儿所。听说他们的儿女现在都早已长大成人了。时光毕竟过去了50年。
为了让我们得到冶金方面的实际体验,方柄先生带我们五个年轻人参观了天津钢厂和唐山钢厂。一面参观,他一面为我们详尽讲解炼钢炉的结构和炼钢的冶金过程。以前,我们从未跨入过钢厂大门,通过这次参观才初识了转炉、平炉和电炉等主要炼钢设备。当时,国外归来的学者少,大学毕业生也不多,所到之处常被礼为上宾,备受热情接待。在天津钢厂,著名的劳动模范潘长有向我们讲了他趁热补修平炉的事迹。我们听了深受教育和感动。四十余年后,在劳动部的一次会上,我又见到潘长有,他已是从天津市劳动局副局长职务上退下的老人了。提起往事,他记忆犹新。我们还参观了唐山铁道学院矿冶系,这是一个著名的院系,冶金界许多老前辈都毕业于这个院系。返京后向李薰先生汇报此行收获时,谈到对唐山铁道学院矿冶系冶金实验室的印象,李薰先生说:“我们将来会有更先进的金相显微镜,设施更加完备的暗室,一切都会有的”。
筹备处的工作百端待举,其 大者是兴建实验大楼,购置仪器设备,采办图书资料,以及日常行政工作,其中重中之重是基建工作。这付重担压在张沛霖先生肩上。张作梅先生负责仪器设备,方柄先生操办图书资料及日常行政事务。我们五个年轻人也相应地做了分工,协助先生们工作。张沛霖先生在回国前,有意搜集了国外现代化实验室的资料。张先生在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各专业实验室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参考、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实验大楼的总体设计方案。从而保证了实验大楼设置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并有许多匠心独具之处。
当时,科学院没有集中的独身宿舍,在各处租用了一些民房,供当年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住。我们筹备处的几个毕业生都住在新街口附近的水车胡同6号。每天早晨我们穿胡同,越小巷到文津街科学院上班,晚上下班多半乘轰隆作响的有轨电车回到住处。吃饭就在院部地下室不大的食堂。在食堂常遇到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先生高高的个子,戴着眼镜,温文儒雅,手柱拐杖,一面排队买饭,一面与人打招呼。钱三强先生在食堂中遇到我们几个人时说:“你们几位的毕业论文,是我和张沛霖先生审阅的,才决定让你们来科学院工作,希望你们给以后再来科学院工作的年轻人打好头阵。”星期天食堂休息,我们就在小食店吃碗阳春面,或在小食摊上吃碗炒饼,吃得心满意足。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中,也不忘忙中偷闲,利用节假日,三、五人结伙尽兴游览古都北京,八达岭的巍峨、太和殿的恢宏、北海碧波、香山红叶都使我们流连忘返。
当年金属研究所选址,有几种方案:北京中关村,有利之处自不待言;沈阳,是重工业中心,东北人民政府所在地;鞍山,是当时国内唯一的钢铁基地,可直接为生产服务。几经磋商才选定沈阳。东北重工业部非常支持在沈阳建所,出资建设实验大楼和多栋宿舍。于是我们要离京北上了。
我们几个刚毕业的学生都是南方来的,衣单被薄,难耐关外严寒。当时实施实物工薪制,我们拿研究实习员最低一级工资, 月薪240斤小米。经张沛霖先生反映、申请,科学院办公厅发给我们每人一笔寒衣补助费。我们兴奋之余,决心做一套厚实的棉衣。经向老北京打听,说最好的服装店是瑞蚨祥。于是,我们兴冲冲地跑到前门,进了瑞蚨祥挺气派的大铜门:只见柜台上摆满各色绫罗绸缎。我们一下傻了眼,不知所措。店员前来问明来意,没有一点轻慢,热情地领我们到楼上一个摆着粗棉布的角落,帮我们挑选了棉布各做一套中意的蓝棉制服。我们又到盛锡福去买皮帽,那里帽子真多,但价格不菲,令人咋舌。于是,只好到早市买。当时北京城墙根下,有多处早市,天色朦胧时开市,都是普通百姓在熙熙攘攘中,选购日用品。我买了一顶便宜的兔毛帽。这套棉服和皮帽又精神又暖和,穿戴了近十年,帮我抵御了北方的风寒。
11月下旬,我们几个年轻人在方柄先生带领下,抵达沈阳,住在马路湾东北重工业部招待所,后迁住东北工学院。当时的东北工学院在铁西旧址,院长是靳树梁先生,冶金系主任是张清涟先生,他们都是冶金界前辈学者,给金属所筹备处许多热情帮助,借了一些房子供筹备处办公和人员住宿,还腾出一栋落成不久的教授宿舍小楼供张作梅、方柄先生两家居住。张先生和方先生都是举国从英国回国的。方先生的夫人叫蒲希莉,是奥地利人。当时,西方国家敌视新中国。可她毅然随方柄先生来到中国东北。一次和方先生聊天中,我们很称许蒲希莉的勇气。方先生不无骄傲地说:“蒲希莉对我无限信任,如果我明天去西藏,她也会毫不犹豫地跟我走。”后来,蒲希莉在金属所阅览室工作多年,非常认真负责,受到人们一致好评。刚来中国时,她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不久,就能流利地与人交谈了。但有时难免用词不当,如一时找不到一本杂志,她会一本正经地说,“这本杂志猫到哪里去了呢?前天我还逮过它。”闲谈中,她告诉我,她的故乡是阿尔卑斯山麓的一个小村庄,风景如画,冬天漫地白雪,夏天满目青翠,在中国住久了,她常常思念故乡。文化大革命后,她携儿女返回奥地利。几年后,方柄先生也移居奥地利。方柄先生在逝世前,多次返回中国,为中奥冶金技术的交流和贸易的发展做了许许多多有益的工作。方柄先生去世后,蒲希莉曾来过中国,旧地重游,感慨很多,她说,下次要专程去访问方柄先生的故乡浙江。做了方家儿媳妇,怎能不去看看方先生的老家,丛山环抱中的建德城,看看方家聚居的老屋,看看方先生童年、少年读书、嬉戏的场所。
12月,李薰先生和各位先生也陆续到达沈阳。筹备处正式在沈阳办公。在东北工学院借住期间,李薰先生曾被盗,损失惨重。我去安慰他时,他坐在椅子上,沮丧地说:“我从英国带回的衣物,都被偷光了。”东北重工业部领导要给李薰先生一些支助,但李先生说,国家也困难,没有接受。
金属研究所筹备处经过在沈阳一段准备工作后,实验大楼终于要开工了。开工前,张沛霖先生领我们参观过南湖建筑工地。工地离有轨电车终点站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要走一段坑坑洼洼的土路,土路两旁尽是冬日的荒芜田野,附近只有沈阳第二中学一座刚落成的教学楼矗立在那里,形单影只,更衬托出周遭的荒凉和空旷。远处,一座建于清朝的古旧砖塔,象一位历史的老人,在夕阳残照中注视着时代的变迁。我正在想,金属研究所怎么会建在荒郊野外呢,张沛霖先生却指着面前的空地说,我们9千平米实验室大楼就将盖在这里。大楼前是座大花园,花园前还有一大块空地,以备将来盖建新楼,集体宿舍和家属宿舍将盖在后面。他又指着右边的空地说,这里将是各种实验工厂。1953年5月,一座现代化的金属科研机构终于正式建成了。
金属研究所实验大楼在紧张的建设前后,一些旅居国外的科学家陆续返回到金属所。
52年,春暖花开时,庄育智先生从英国回来。当年才28岁,一派儒雅的学者风度。他虽然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由于他的学养和人品,我们从心底里尊他为长者。念大学时我没学过冶金,初进实验室,茫然不知怎样做实验。他耐心教我如何将一块粗糙的钢铁磨成镜面一样光滑的金相试样。又教我用金相显微镜分辨钢铁的各种组织,是他带我步入金属研究的领地。1953年,抚顺一家炼油厂发生重大爆炸事故。庄育智先生带我深入爆炸现场观察采样,又在实验室做分析研究,得出了科学结论。
90年代初庄育智先生在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院担任名誉院长。同时还在华南理工大学和金属所分别指导多名博士研究生。经常风尘仆仆地奔波于京、沈、穗三地。乘坐的往往是火车硬席。我曾劝他年逾古稀不宜再乘坐硬席火车,坐飞机便捷些,或坐软卧舒服些。他却以为课题经费有限,应尽量用于实验上。庄育智先生一贯自律甚严,几近苛待自己,终于为科研事业劳瘁而逝。
52年秋天,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之际,葛庭燧先生与何怡贞先生来到金属所。在随后的几年中师昌绪先生、郭可信先生、斯重遥先生、吴鼎铭先生都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先后从国外来到金属研究所工作。一时,金属研究所材料科学的天穹上,群星璀灿,光辉夺目,其光芒所致,远远超出了金属科学研究的空域。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科学家无一例外地被关进牛棚,备受凌辱,其中55年由美国归来的师昌绪先生所受的迫害最为酷烈。师昌绪先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稳定工作,生活优越,但他冲破重重阻力毅然返回祖国。他对人忠厚仁慈,谦和体谅,从不疾言厉色。我有幸随他工作十余年,所受教益,难以言表,清夜思之,不胜感激。文革中师昌绪先生肉体愈受摧残,生命之力就愈益昂扬,清白越遭诬陷,人格尊严的意识就越发觉醒。这正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热爱真理的正直科学家在身处逆境中显现出来的精神品质的光辉。文革后师昌绪先生以更旺盛的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科技领导和研究生培养的繁重工作中。
99年师昌绪先生八十大寿,金属研究所召开隆重的祝寿会,我重病在床,未能亲致祝贺,常抱憾在心。病榻上思得贺联一首,也未能寄出,谨录于此,聊表我心。
学富德高,历尽艰辛,研究精深,煌煌业绩铸高峰。
奖掖提携,待人至诚,春风遐被,芸芸后学寿乔松。
历史不会忘记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在金属研究所的职工名册上从未出现过他的名字,但他却一直参与了金属研究所的筹备和兴建。他就是柯俊教授。酝酿筹建金属所时,他在英国参与规划。李薰、张沛霖两位先生回国后,他在英国又代为购置建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和资料。柯俊教授回国后,在高等学校工作,几十年来,他一直关心金属所的建设和发展,金属所的许多优秀科研人员,都是他的亲炙弟子。
历史还不会忘记焊接专家姚桐斌先生。当年他在英国曾约定来金属研究所,也为金属所早期筹建做了不少工作。回国后被分配到国防科工委所属一个焊接所当所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为科学家的他,被造反派用大木棒猛击头部而身亡。文革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纪念他。人们对这位科学家的惨死悲愤不已,追思不已。
1984年,我随庄育智先生调离金属研究所。回首遥望,在金属研究所工作了三十三年。我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步入了人生的暮年。这三十三年,有坎坷,有风雨,但却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年华。我深自庆幸能师从那些可尊敬的长者。他们的道德文章,他们的智慧胆识,他们的胸襟风骨,他们的爱国赤诚,他们卓越的科研成就,他们对真理的孜孜追求,他们在文革中虽身处逆境却永不改初衷的坚贞,他们对年轻人成长进步关怀备至的殷殷之意和拳拳之心,在在都使我感佩不已,铭刻于心。他们的言传身教,熏陶培养让我懂得如何做事,怎样做人。如今,这些长者有些过了耄耋之年,但精神矍烁,毫无龙钟老态,仍活跃在科坛上。我在病重之际,衷心祝愿他们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李薰先生、方柄先生、吴鼎铭先生、庄育智先生、张作梅先生都已离开我们,长者其萎,思之凄然。他们在中国材料科学史上都留下一串长长的、深深的脚印。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跟随李薰先生多年的张子青,由于他秉性耿直,口无遮拦,被错划成右派分子。80年平反后回到金属研究所。见面时,他送我一张已泛黄的旧照片,是当年金属研究所筹备处全体人员合影。51年11月下旬,金属研究所筹备处迁往沈阳的前夕,有人提议合影一张,于是在科学院花园前摄下了这张照片。张子青被错划右派后,颠沛流离二十余年。书籍、衣物损失殆尽,却还珍藏着这张照片。其实,他珍藏的是对长者、对同志,对科研事业深切的眷念,他珍藏的是金属研究所历史发展中一个有意义的片断。
今年初,我给张子青写信说,你保存的那张金属所筹建初期九人合影,当今年秋风又起时,就已经五十年了。照片中尚存的人,再过五年会怎样呢?再过十年又将如何?这句话似含伤感,其实,我想说明一条千古不易的自然法则,了无凄情。唐朝诗人刘禹锡说得好:“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新叶总是更鲜活,更有生命力;后波也会更汹涌,“来者尽翘翘,前峰喜更高”。我想,这正是长者殷切的希望。
附记:这篇文章由我口述,老伴白德昆笔录、整理。我大病卧床已近两年,如果没有她的帮助,这篇文章是断乎写不成的。谨致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