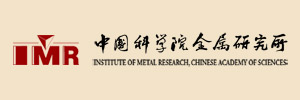我们敬爱的李薰所长离开我们整整十八年了,他的过早去世使我国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冶金学家,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十多年来每当我出差回金属所去李薰像前瞻仰时,总使我想起李所长生前对我的培养与教诲。现仅就原子能冶金的前前后后作一些点滴回忆,以表示对李所长深切悼念之情。
李所长坚持科研为经济建设及国防建设服务的思想是一贯的。李所长将金属所选址在沈阳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要金属所为沈阳周边的鞍钢、本钢、抚钢等钢厂的钢铁生产服务,建所初期的选矿、耐火材料、氧气炼钢,钢中气体夹渣等都是为了当时钢铁生产需要而开展的工作。60年代初期由于国际科技的发展及国家国防建设的南非要,李所长当机立断把金属所主要为钢铁工业服务的研究方向转变为新材料为国防尖端技术服务为主的方向,60年代初期接受原子能冶金则是李薰所长坚持科研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服务的又一次集中体现。6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的苏联领导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使我国新生的原子能事业处于极端困难之中。当时李所长明知金属所并不具备开展原子能冶金的条件,但当科学院领导找到李所长时,他急国家之所急,毅然把这一光荣而艰巨任务承接下来。在李所长的领导与支持下,立刻抽调了所内近百人的科技队伍,迅速组建了两个研究室,即铀的化学冶金研究室(15室)及铀的物理冶金研究室(10室),他还亲自兼任15室的主任,而十室的主任则由副所长张沛霖兼任。除两个研究室外还有化学分析、铀的压力加工等研究组也参加工作。
我就是当时被抽调参加铀冶金最早的一员。我的原专业是冶金物化,研究方向则是炼铁,由于金属所炼铁组早已与北京化工冶金所合并,所内也已明确将我调往北京化冶所工作。记得是6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李所长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谈起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说到苏联专家撤走,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干我们自己的原子能事业,金属所要急国家之所急承担铀冶金任务等,希望你也参加此项工作。当我还在思索考虑的时候,李所长就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你不去北京化冶所了,留下来干国家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原子能事业。”我见到李所长那种坚定的神态,我二话未说,就满口答应,我愿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奋斗,决定不去北京化冶所了,这是李所长对我科研生涯的第一次抉择。
十室十五室成立于苏联专家撤走三年困难时期,以李薰所长张沛霖副所长为首的一批科学家们义无反顾地决心要把我国年轻的原子能事业搞上去。当时的这种政治形势,自力更生奋斗图强的呼声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爱国热情,尽管物质上当时极端困难,但思想上精神上都信心百倍,一定要为我国原子能事业争气。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铀的热还原、铀的真空精炼、压力加工、铀中气体夹渣、铀的物理性能测试、密封包装以及铀的化学分析等都相继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实验室,并初步开展了各方面探索工作。为了更加明确研究任务,李所长以及党委初步开展了各方面探索工作。为了更加明确研究任务,李所长以及党委书记高景之副所长,还先后几批带领有关的科技人员去铀的生产基地考察、调研、与厂的领导及科技人员共同探讨科技攻关事宜。
铀冶金对当时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陌生的领域,根据有限的资料李所长在15室安排了铀的热还原、铀的精炼以及铀中气体夹渣的研究。在整个工作中根据他在国外多年科学研究的经验,经常教导我们科研不但要解决“怎么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需要解决“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问题。实际上他要求我们在解决任务的同时要做些结合任务的应用基础性工作。根据他的思想我们曾安排了合金蒸汽法测定、炉渣黏度测定、铀的表面张力及黏度的测定等工作。他还经常教导我们,热衷于炒菜式工作是没有出路的,这种工作表面上似乎很快,实际上提不高科研水平,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他还要求我们要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仔细分析文献资料是会找出办法来的。所有上述教导使我们收益非浅。
我们当时承担的具体任务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08核燃料元件的试制及攻关,另一是09核燃料元件的试制。
在经过几年实验室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于1965年1966年曾先后几批派了大批科技人员下厂与厂方一道参加08核燃料元件试制工艺的最后攻关,并最终取得圆满成功。为此于1986年金属所曾获得国家特等科技进步奖(覆盖奖)。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项工作均处于停顿状态,但原子能的研究工作并未停止。在此期间,我们还进行了镁热还原生产金属铀的工艺研究,高强度铀合金(U-Mo合金)的研究,以及型改进生产堆铀元件的探索工作等。虽然上述工作并未在生产上推广应用,但上述工作对整个原子能事业还是有意义的。
1970年是金属所开展铀冶金研究的十周年,由于当时三线建设的需要以及金属所污染面的迅速扩大,沈阳市已不再允许金属所继续从事铀冶金的研究工作,整个金属所的原子能冶金部分面临着调整搬迁。经上级决定金属所与原子能冶金有关的科技人员迁往成都效区与二机部有关单位合并成立西南原子能研究院。正在这一体制进行重大调整之际,我被当时的所革委会宣布调入教学连作教学工作,同时被调去的还有师昌绪同志等。此时我已意识到我可能不属于这次调往三线名单之列,已被打入另册。由于我从事铀冶金多年,对这一研究方向已发生浓厚兴趣,所以仍不死心地向李所长(当时是所革委会副主任)打了多次请调报告,希望批准我去三线工作,但结果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至1971年待全部同志都已调走,并得知当时三线建设的困难情况后,有一次李所长见到我,问我现在还想去四川吗?我立刻意识到,我当时写的几次请调报告他是很清楚的,当时不作回答,无非是给我冷处理,目的是希望我留下来在金属所继续工作。在教学连工作一年多,于1972年上半年,李所长又决定把我调回8室,明确我负责钛合金的研究工作,并进一步明确我们集中搞航空用高温钛合金的研究,不搞其它钛合金研究,这一安排与当时金属所搞航空高温合金的工作相配合,使金属所又增添了一个更好为航空工业服务高温材料的生长点,这是李所长精心安排的结果。这也是李所长对我科研生涯的第二次抉择。
我科研生涯的第三次抉择是1985年,是我调往上海大学,这一抉择是李所长逝世后我自己作出的错误抉择,虽然不是李所长决定的,但这次抉择仍与李所长有关,如果李所长不过早地在1983年离开我们,他是不会同意我离开金属所的。
------------------------------------------------------------------
1983年3月16日是我与王中光同志作为访问学者飞赴美国的日子,记得3月15日晚李所长为了欢送我们邀请我们在他家吃晚饭,同时还有王仪康同志,他将陪同李所长去攀枝花钢铁公司考察,没有想到他在行经昆明途中,突然与世长逝,这一噩耗是同年4月份我从海外版人民日报上得知后,我十分悲痛与惋惜。
我们永远怀念李薰所长!